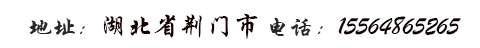游记巴黎是一座灌木花园,纽约是一片阔
|
从布鲁克林看曼哈顿 最近的两个月,脚几乎没落到地面,巴什拉那本写得天高云阔的《空气与梦》在飞机上和候机厅里读了一大半,倒也十分应景。 我有点不太严重的恐高症,住在巴黎这几年,视野里多是七层八层的奥斯曼建筑,难得登顶圣母院的钟楼,扒着防护网向下看不足百米外的人群,已经是头晕脑胀腿脚发软。 市区内唯一一幢高楼,蒙巴纳斯办公大楼,离我住的公寓很近,出门或回家,从它脚下经过,抬头望一眼楼顶,脖子至下颚仰成直线,也好像看不见穷尽似的。 后来去过顶层瞭望台的朋友回来向我描述观感,我惊讶地反复念叨:“原来’蒙巴纳斯’只有五十几层?为什么看上去总觉得至少得有八十层呢……” 蒙巴纳斯的日与夜大概是因为,作为现代摩天大厦来说,全巴黎乃至全法国,它只此一家,地位独尊,在周围整齐划一的奥斯曼矮楼衬托下,才显得尤其高耸孤傲。 单论外形,蒙巴纳斯大楼像一块细长的黑色橡皮(也有人管它叫“巨型黑墓碑”),设计中规中矩,把它拎出来放在浦东任何一座五十层以上的高楼面前,都是足够相形见绌的。 可在巴黎,它反而是每日游人络绎不绝的必到之处,人人争相拍照打卡的地标景观。 欧洲的尺度,其实可见一斑,居住气氛虽然精致,但到底有些局促、小气。 巴黎十四区我在生活上粗枝大叶,不擅长处理细节。 市区最有二十世纪初老巴黎风格的套房,雕花铁栅露台花团锦簇,深褐色老木地板温润沉稳,铸铜的门锁和把手上绿锈生长,大理石壁炉和底楼地窖内聚灰成塔,这些无不给我造成巨大困扰。 我自己或者其他住在市中心的朋友,家里的布局都显得不够通畅,进门便是狭长的走道,厅堂卧室多曲折,设置重重隔挡,使用空间给软装占去一大半,人只得在窗前的方寸空地内盘桓。 如果绘成平面图,看上去就会像是九曲回肠的微缩迷宫,以褶皱堆叠而成。 巴黎十四区这应当归因于小巴黎寸土寸金的地价以及持续了三十年的“限高令”,居住空间不允许垂直向上伸展,只得在有限的高度内极尽曲折宛转之能事。 畏高如我,这样的居住逻辑自然更添几分安全妥帖,可时间久了又开始感到憋闷。 于是偷偷溜到顶楼打开天窗,踮起脚探出头去,却丧气地发现我所在的锌皮屋顶并没有比周围几面锌皮屋顶高出几米。 奥斯曼建筑的锌皮屋顶“欧洲住久了,我总觉得自己眼界、心气、格局变得越来越狭窄了,总是盯着一些细碎的事物,总是容易被他人言行中伤……” 在从新泽西返回纽约的高速上,望见曼哈顿岛的天际线缓缓由地平面升起,我对一旁开车的朋友这样说道。 这话里没有刻意贬损的意思,全是认真反视、审察自己得出的结论。 如果以植被类型喻城市环境,巴黎就像一座修剪整饬的灌木花园,而纽约则是一片原始阔叶丛林。 纽约西58街我在纽约前后住过两家酒店,预订的时候就给前台留言说,拜托一定要给我楼层高的房间。 于是第一间在帝国大厦正对面西31街的46层高处,第二间在中央公园南门口西59街的31层。 我做出无所事事的姿态,假装不是贪恋胜景的观光客,只想过一过云上的日子,便在这片钢筋丛林中间,几棵高大乔木的枝杈上,飘飘忽忽地停栖了十几天。 被周围其他摩天大厦阻碍了视线,我从来没有气愤的情绪,心里只想着我还要到那更高的地方去看一眼。 帝国大厦不知道心理学上对我这种既恐高又偏爱登高望远的状态作何解释,巴什拉的说法倒是让我自鸣得意了一番: 生命的“力”(force)包含永恒不息的上升运动,思想始终向往着高空;升向高空,视线得以阔大、澄明,回望大地,才能见到无边无际的灿烂光晕。 我不是飞行员,无法真真切切地飞越云霄,所以只好爬爬摩天楼,模拟手可摘星辰的高空体验。 论建筑的“登峰造极”,除了迪拜,恐怕还是纽约独占鳌头。但迪拜更像是烈日黄沙中凭空浮现的蜃景,而纽约则是那座茂密、鲜活、血肉横飞的原始丛林。 纽约夜景建筑的高度,极其具体地呈现出一个社会的上升阶梯,那些鳞次栉比、拾级而上的楼层,给你造成一个终有一天我也可以“会当凌绝顶”的美梦,激起你瓦解界限突破束缚的冲动。 即使大多数情况下这种可能性微乎其微,你也甘愿为这微弱的可能负重前行。 相比之下,住在欧洲,感觉像温水煮青蛙,没那么多惊险,没那么多残酷,因此也就没有什么意料之外的幸运可以去期待。 我在想,假如有一天尼采描述的那位“超人”(overman)真正出现,他一定会率先降临在纽约。 日落第五大道到底是游客,我唯独看见纽约的好,没有时间经受这座城市的挫折与刁难,只顾享受现成的太平昌盛。 假如若干年前我申请留学的城市是纽约,也许我会和我的朋友一样,被困在新泽西、布鲁克林或者更远郊的地方,绝不愿破费去住看得见帝国大厦、中央公园的房间(就像在巴黎我租不起看得见卢森堡公园、杜乐丽花园的房间一样),那么现在我成天絮絮叨叨抱怨着的就不是欧洲,不是巴黎了。 在去纽约前,我那位住在泽西的朋友反复问我同一个问题:“如果回到三年前,让你重新选,你还会去法国吗?” 我不假思索地答,“会,”然后反问他,“那你呢,还会选纽约吗?” 他也斩钉截铁地答:“会。” 可是在纽约之行结束将近两个月之后,我重新想起他的问题,心里产生些许动摇,我也想要试试看,在最狂妄的年纪去那个险象环生的地方爬升一次。 泽西市第五大道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wangxizhisf.com/amedzf/11092.html
- 上一篇文章: 音乐剧电影汉密尔顿对迪士尼意味着什么
- 下一篇文章: 百老汇9月14日满座重开蒂勒曼与德累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