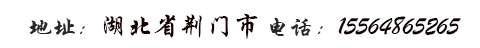刘擎2019西方思想年度述评上篇世界
|
白癜风可以治好么 http://pf.39.net/bdfyy/dbfzl/160319/4793212.html 上篇·世界变局 序言:近身的世界 脆弱的新共识 中篇·欧美风云 弹劾与分裂 新的雄心与危险 下篇·思想前沿 面对全球气候紧急状态 优绩主义的陷阱及其教训 资本主义的未来 序言:近身的世界 告别年,一个年代(decade)落下帷幕。新世纪迈进第三个十年,世界的面容仍晦暗不清。混沌与动荡经年已久,大变局中的人们或许不再惊慌,但却难以辨识,更无从把握自身的“时代精神”(Zeitgeist)。可谁还会在乎老黑格尔的陈旧概念?既然历史目的论早已被时尚思想抛弃,时间之矢也就无所谓确定的方向。 柏林墙倒塌三十周年,德国在11月举办系列纪念活动。福山在柏林墙遗址前接受《德国之声》采访,他对“历史终结论”毫无悔意,并坚信“推倒柏林墙的精神长存”。云集的欧洲政要们在谈论“冷战终结”的意义,而与此同时“新冷战”的言说已经甚嚣尘上。已经终结的历史斗争似乎正重新开启。 可是“End”一词不只是“终结”还有“目标”的涵义。福山自己说过,他也是在双重意义上将这个词写入他的书名,因此“历史终结论”也就是“历史目的论”。黑格尔和马克思相信,时间是一个矢量,世界历史有其方向,终将达成人类共同的目标。福山只是这个思想传统晚近的继承者,他认为在历史观的意义上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并声称这是中国人不太容易误解他的原因(可是他偷换了马克思确定的最终目标!这解释了为什么中国人不会喜欢他)。现实进程中的历史“故事”远未终结。但福山的问题是,我们何以能就此断定世界历史(人类的故事)不会有共同的目标? 因为共同的目标依赖于汇聚或趋同的经验证据,福山曾坦言他受到上世纪中叶“趋同理论”(convergencetheory)的影响。但当下的现实世界遍布着汇聚的反例:英国脱欧、美国退守、WTO上诉机制失灵,NATO成员争议四起,经济和政治的民族主义勃兴、分离主义、反移民和排外浪潮的汹涌、贸易争端的加剧,以及全球化的衰落(似乎只有中国仍然积极推进全球化,并畅想人类的共同命运)。的确,在过去的一个年代,我们见证了历史方向的逆转,分裂与离散开始主导时代潮流。人们讲述着各自不同的“小故事”(历史),而“大写的历史”及其目标似乎已消失隐匿。 政治理论家沃尔夫(AlanWolfe)在《新共和》发表书评,为福山的新书《身份认同》 Identity () 而惋惜,断定这是昙花一现的著作。他赞叹三十年前的那部名著,称之为“大观念”之作,虽然论点错误,却石破惊天、足具份量。正如马克思哪怕错了,也不会是“次要的后李嘉图主义者”。沃尔夫哀叹当下缺乏大观念著作,期盼那种能在纷乱谜团中为人辨析引导性线索的作品。 但大观念之作再次出现了。 经济学家米兰诺维奇(BrankoMilanovic)在9月出版新著《唯有资本主义》 Capitalism,Alone () ,阐述当今世界已汇聚在同一经济体系中,它的语汇成为世界各地的通用语言。米兰诺维奇的论题像是打了半折的终结论,砍去了福山版本中的自由民主制,留下资本主义经济作为世界体系的框架。他论证指出,目前最主要的冲突与竞争汇聚在这个体系内部,只是发生在其东西两种变体之间,“自由优绩制的资本主义”(liberalmeritocraticcapitalism)以及“政治的资本主义”(politicalcapitalism)。两种形态都有各自特点的缺陷,但处在同一体系之内,它们共同的演化将塑造未来几十年的世界历史。这个体系创造了巨大的生产力和利润,但在社会平等和道德状况方面相当令人堪忧,这正在侵蚀健康的自由主义价值观及其政治理想。或许,目前的现状只是通向更好世界的道路中一段崎岖坎坷的阶段,正如十九世纪粗鄙资本主义的改良过程。但这种进步可能没有历史必然性。 Capitalism,Alone 封面 姑且不论他使用的范畴是否恰当,米兰诺维奇在分裂与离散的潮流中提出了一种汇聚的论述,这与人们的现实感大相径庭。我们熟知的常识是“冲突导致分裂和离散”,“共通才会汇聚和融合”。这位经济学大师似乎缺乏常识。 然而,人类的大历史恰恰(主要)是一部“冲突而汇聚”的历史,更确切地说,是一个“经由冲突、达至共通、终于汇聚”的故事。这是林肯南北战争和战后重建的故事,也是欧洲经由二战、战后和平进程、最终走向欧盟创立的故事。 当下的冲突与离散趋势,恰恰因汇聚本身而起。全球化过于迅即、也过于紧密地将原本相距遥远的生活方式联系起来,纳入同一个复合相互依赖的体系,可称之为“近身的世界”。但这个世界并不是一个“地球村”(麦克卢汉只说对了一半),而更像是“地球城”,汇聚的人们来自不同的“村庄”,带着千差万别的方言、习俗与信仰。差异让生活变得丰富多彩(这是许多人偏爱城市的原因),但也埋伏着冲突的隐患。 疏远的人们可以漠视差异,在遥遥相望中和平共存。但在近身的世界中,彼此迂回和缓冲的灰色地带大大收缩,差异更可能引起分歧,矛盾难以调和,冲突容易加剧(从前完全无法想象,某个运动员的一条推文就足以激发抗议和反弹,掀起一场话语对抗的风暴)。于是,“脱钩”成为一个似乎现成的选项。 但我们很难离开这个近身的世界,或者付出的代价不可承受。正如厌恶城市的人们在踏上返乡之路后,很快会发现记忆中的乡村已面目全非,越来越深入地被织入了城市之网。无论在积极或消极的意义上,相互依赖的进程仍然在不断加深。在米兰诺维奇看来,这是 仅存的世界。 在这个意义上,离散并不是汇聚的反题,只是汇聚不良的应急症候。因此,“受不了你,却离不开你”(Can’tlivewithyoubutcan’tlivewithoutyou)这句流俗的台词正是我们“时代精神”的侧影,我们完全可能只是处在“冲突而汇聚”的曲折进程中。是的,历史是有方向的,但并不直线前行,黑格尔和马克思都这样说。 但米尔斯海默(JohnMearsheimer)不会同意。他相信冷战之后的自由国际秩序只是“大幻觉”(TheGreatDelusion),至多是短暂间奏,世界再次回归冲突的时代,这是政治的常态。这位现实主义理论大师声称,在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的每一次交战中,几乎都是民族主义获胜。他甚至提出了哲学论证:自由主义失败的缘由在于其个体主义的哲学基础,但这是错误的哲学,因为人类“天生就是社群动物”(他邀请了亚里士多德来点赞),必定依赖于共同体而生活。 不过,按照这位理论大师的“政治哲学”,人类至今还会生活在宗族、部落至多是封建王国的政治社群之中。对于部落人而言,民族国家(更不用说欧盟)完全是妄想的乌托邦。如果人类可以突破部落,走向民族国家“想象的共同体”,那么为什么“想象”必定到此为止?为什么民族国家是政治共同体 和最终的形式。米尔斯海默对当下国际冲突的洞察并没有错,但这是依赖特定时代条件的历史政治学解释,本不必用半吊子的哲学伪装成一个“大观念”。 《大幻想》封面 无论如何,这个时代在经验意义上呈现出离散与汇聚的双重性,或许很难断言哪一种才是大趋势。谁知道历史有没有方向?说不定古人说的对,历史是循环的,而历史的线性进步只是启蒙哲学家的幻觉。但是,今天让人们汇聚的力量不只是美好事物的吸引。全球气候危机,极端主义势力对安全的威胁,高新技术发展的多种挑战,以及在世界大部分地区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所有这些都不是民族国家能够单独解决的问题。即使在负面的意义上,人类也分享着共同的命运。汇聚不必因为彼此喜欢,而是因为面对着无法独自应对的共同问题,这要求在竞争中保持对话与合作。 那么,“新冷战”是无可避免的吗?有人相信甚至期待“注定一战”,因为《左传》早就说过“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可是,后来陆九渊又说“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中国的传统智慧是如此丰富,让离散与汇聚都会有据可循。但如果米兰诺维奇是对的,如果双方已经处在同一体系之中,那么“新冷战”将是一场(与旧冷战完全不同的)“世界内战”,这大概需要在哈贝马斯所说的“世界内政”(Weltinnenpolitk)的框架中才得以恰当理解以及应对。 未来会怎样呢?中国智慧也穷尽了不同的可能:“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这是高明的见解。但罗贯中没有读过《人类简史》,看不清长久而缓慢的变量。在大尺度历史的研究考察中,赫拉利(YuvalNoahHarari)发现“合久必分只是一时,分久必合才是不变的大趋势”。 脆弱的新共识:美国对华战略的分歧 “你听到的撕裂声,是两个巨大经济体开始脱钩的声音。”名作家弗里德曼(ThomasFriedman)感叹着。他曾期许一个不断“变平”的世界,而今却惊讶于它日益醒目的折痕。《金融时报》将“脱钩”(decoupling)选作年度词汇,因为“美中关系的蜕变可能是我们时代最重要的经济事件”。 FT年度词汇 变迁的节奏出乎意料的迅即。“新冷战”之说不久前还像是可疑的传言(一年前BBC文章的标题称之为“耸人听闻”),到了年已被许多论者当作既定的事实。 “中美国”(Chimerica)一词的发明者弗格森(NiallFerguson)教授坦言,“在短短一年间,美国人对中国力量增长的恐惧骤然上升。曾经只是少数危言耸听者的立场,现在成为华盛顿的新正统。”他3月在《星期日泰晤士报》发表文章,反省自己“读了太多的基辛格”(作为基辛格“钦定”的传记作者),而忽视了老朋友艾利森(GrahamAllison)教授警告的“修昔底德陷阱”及其“注定一战”的前景。他相信,“虽然我们未必注定要打一场热战,但我们肯定是走上了一场冷战之路。” 他12月在《纽约时报》的文章正式宣布:“中美国”所描述的伙伴式共生经济关系已不复存在,第二次冷战在年已经开始。他认为,新冷战未必是坏事,肯定好过默许对方接管世界,而且还有可能缓和美国内部的政治分歧。至于美国能否再次赢得冷战,弗格森完全没有把握,因为今天中国带来的挑战远非昔日的苏联能够相比。他预期“这场新冷战会变得更冷”,而且将会比特朗普的任期长久得多。 面对剧变的节奏,聪明的弗格森凌乱得露出了机会主义的底色。而矢志不移的理论大师米尔斯海默则如少年般容光焕发。从其名著《大国政治的悲剧》问世以来,他一直几乎孤独地呼喊着“狼来了”,十八年之后终于等到了他期待的“狼”,也迎来了“进攻性现实主义理论”的荣归时刻,将在国际政治理论中重新压倒充满幻觉的自由主义理论。七十二岁的米尔斯海默年在世界各地(包括中国)“巡演”布道:“自由国际秩序”(如其近著的书名所言)是“大幻觉”,只可能在一个自由国家主导的单极世界中短暂存活,而中国的崛起打破了单极格局,注定会导致新的竞争与冲突。 这里没有什么是非对错,而是国际政治“零和博弈”的冷酷逻辑使然,大国必定会伺机扩张,寻求区域霸权,进而引发大国间冲突。因此,冷战后的自由国际秩序“从开始就注定失败,因为它包含着自我毁灭的种子”。8月在澳洲“独立研究中”(CIS)举办的辩论中,当被问及“新冷战”是否会来临,他明确回答说“我们已经在新冷战之中了”。在 学术刊物《国际安全》春季号发表的论文中,米尔斯海默意味深长地写下一行小标题:“TheLiberalInternationalOrder,-”,以墓志铭的格式宣告了这个秩序的寿终正寝之年。 年底传出消息,中美即将签署 阶段贸易协议,但这个好消息既来得太迟、似乎也不足够好,安抚焦虑尚可却难以振奋人心。年伊始,《经济学人》推出了封面专题“两极分离”,告诫人们,“不要被贸易协定所迷惑”,因为“地球上 的裂变”正在发生,“两个超级大国的分裂将会完全改变世界经济,而代价之高难以想象”。 《经济学人》封面 无论以“新冷战”还是“脱钩”来判定当下的势态,都暗示着中国与美国的激烈竞争乃至对抗将成定局。但是,过去三十年的历史见证了太多论断,起初言之凿凿,转瞬过眼云烟。焦虑不安的时刻很容易对盘根错节的脉络失去耐心,并将仓促的惊人之语误作深刻的洞见。 美国的对华政策将会转向全面的“遏制”(containment)战略吗?这取决于对中国的认知。冷战之后西方对于中国的发展存在三种主要的论述:崩溃论、演变论与威胁论。它们相互竞争,此消彼长地占据主导地位。崩溃论者不相信中国会发生亲西方的改变,但将赌注压在中国发展的有限时效性。每年都有分析家考察中国经济的结构性危机以及政治隐患,预言这种高速成长不可能长期持续,最终会走向崩溃。演变论者认为,中国在进入自由国际秩序之后,必定被这个秩序所约束和塑造,终将实现和平演化,虽然未必走向“西方化”的道路,但至少能够与西方维持互补合作、良性竞争以及和平共存。而威胁论坚信,中国强劲的崛起以及反西方立场都不可能改变,因此迟早会对美国(乃至整个西方世界)构成严重的威胁。 如今在华盛顿的精英看来,“崩溃”希望渺茫,“演变”遥遥无期,于是“威胁”便成为关于中国的主导性论述。但需要指出的是,崩溃论和演变论虽然衰落却没有灭绝,若今后卷土重来也不会令人意外。 那么,弗格森所谓的“华盛顿的新正统”是什么呢?近两年来,一种“新共识”在西方政界与思想界流传:美国以往基于演变论的对华“接触”(engagement)战略失败了。不断崛起的中国并未按照西方所期望的那样,温和地融入美国创立并主导的国际秩序,而是成为挑战这个秩序的“修正力量”,已经造成了严重的威胁。因此,现在应当放弃过去温和的接触战略,代之以更为强硬的方式以“规制”中国,这是美国发起 的理论基础。许多评论家认为,这是当下美国分歧严重的两大政党精英之间罕见的(甚至 )的共识,也是美国外交界、智库以及学术界许多人士的共识。 然而,这种共识会是可靠的吗?老基辛格曾对共识问题有过评论。在二战之后,美国卷入的大多数(对朝鲜、越南、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战争,最初都获得了两党广泛的支持共识,但“随着战事的发展,国内对战争的支持开始瓦解。然后达到了一个转折点,退出战略变成了主要的辩论议题”。他就此总结出一个原则性的教训,“如果进入战争只是为了 有一个退出战略,那么当初就不应该在那里开始。”这是基辛格年在威尔逊中心一次演讲的开场白。八年之后,在中国贸易谈判僵持的时刻,基辛格再度访问北京,他这番洞见格外令人回味,对中美双方都是如此。如果发起“新冷战”最终只是为了停战,那么今天就不应该开始。 基辛格 当前华盛顿的新共识很可能是短暂而脆弱的。至少,在年的大量相关讨论中,已经出现了许多质疑的声音。首先,三十年来美国的对华政策是否可以化约为单纯的接触战略?其次,这种政策是否真的完全失败? ,也更重要的是,什么才是恰当的替代性选项?在笔者看来,一个未被明述却更为致命的反诘是:即便接触战略的失败是一个事实,这本身在逻辑上并不意味着其他选项(比如“围堵”战略)将获得成功,或者不会导致同样的甚至更加严重的失败。这种深层的不确定性,塑造了当前各种对策提案的竞争性、尝试性和暂时性的基本特征。 实际上,目前的所谓共识主要是消极性的,就是承认必须反省以往对华战略的失误,但并未达成关于“应当如何应对中国挑战”的积极共识。正如蓝普顿(DavidLampton)所指出的那样,当接触政策已经不复存在,就会出现对于引导性政策的竞争。 在混乱的争议中,我们仍然可以辨识“强硬派”与“审慎派”的不同取向,他们在如何认识与应对中国的问题上存在明显的分歧。 强硬派的基本取向是坚定“对抗中国”,在媒体、智库、国会和白宫中都有其代表,有些是传统的鹰派人士,也有些是幻灭后的演变论者。最近一个值得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wangxizhisf.com/amedqh/11019.html
- 上一篇文章: 巴尔干半岛最美丽的10个城镇遇见不一样
- 下一篇文章: 天津艺术设计考研,图优优陪你一起学习